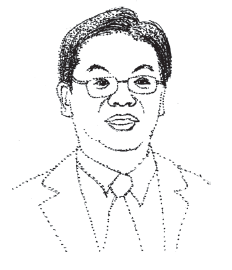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有一套完整系统,其中乡约扮演了重要角色。乡约诞生于乡村社会,从以德教化为主,逐渐发展成为统筹乡村诸多实务的综合治理平台,在稳定乡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约起源
乡约,也可以称为“乡规民约”。规,强调的是规矩;约,强调的是约定俗成。对于乡约,《辞海》解释为“同乡人共同遵守的规约”,《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为“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在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的中国古代, 由于人员流动性不高,因而形成了“熟人社会”,人们在执行国家法律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协调生活秩序和社群关系。
早在周朝,就已出现了乡约雏形。《周礼·族师》有一条记载: “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 以相葬埋。”大意是:在地方上以5家组成一比,10家为一联;在军队里以5人组成一伍,以10人为一联; 在地方上以4闾组成一族,在军队里以8闾为一联,使他们相互担保托付,有刑罚、喜庆、赏赐的事共同受享,这样来承担王国的职事,为国家服役,遇丧葬之事相互帮助。将百姓结成比、族,大家互相帮扶和监督,这种约定初步具备了乡约的一些特征。
到秦汉时代,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三老”的设置。“三老”不是3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而指的是一个人,因其通达《尚书·洪范》中所讲的正直、刚、柔三德而得名。《汉书·高帝纪》记载:“举民年五十以上, 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根据这项记载,汉朝在每个乡设“三老”一人,在县里也设有一名“县三老”,除了年长、有德行外,最重要是“能帅众”,在乡里有足够威望。汉朝的“三老”不是国家正式官吏,身份还是民,但“非吏而得吏比”,其中“县三老”的地位堪比县令、县丞,《汉书》称其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除教化乡民外,“三老”还承担乡村祭祀、协助赈灾、动员徭役等职能,朝廷和官府还常就乡村治理向“三老”咨询。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贤能之士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与治理中。东汉京兆下邽人王丹“资性方洁”“家累千金”,但不喜欢为官,官府“连征不至”。王丹后来致力于乡村建设,《后汉书·王丹传》记载:“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根据这些记载,王丹在乡间以身作则,用奖惩措施来引导乡民教化,乡民对其一些做法慢慢习以为常,虽未留下成文约法,但也可以视为法学上所讲的“习惯法”, 即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
汉朝的“三老”设在县、乡, 乡以下的里还有“父老”。东汉学者何休指出“父老比三老、孝悌官属”,并在注释乡村基层组织状况时说:“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1973年,河南省偃师县缑氏乡浏涧河南岸出土了一通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 共213字,记述的内容是,东汉缑氏县侍廷里左巨等25户人家集资6.15万钱买田82亩,组织起一个叫“僤”的民间团体,以解决本里与“父老”任职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有人把这通石碑所载的内容认定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成文乡约。
德业相劝
早期的乡约虽然具备相应的属性与形式,但作为成熟的、广泛应用于乡村治理的规范则出现在宋朝。宋朝实行文治,在统治思想方面,将汉朝以来的儒学进行了革新发展,标志是理学的兴起。与传统儒学相比,理学更注重乡村建设与治理,强调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教化导民、化民成俗,真正达到“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治理效果。
关中是宋朝理学重镇,关中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名言被称为“横渠四句”。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张载强调以德育人,认为人本性无不善,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而有不善。为使人为善,必须通过教育、学习来变化气质、返本为善。张载强调“幼而教之,长而学之”,认为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 反对学而不用、坐而论道;提出所谓“圣人之学”应以排除国家民族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和人民为忧患是没有用的。
张载所创立的“关学”影响巨大,京兆蓝田人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兄弟相继拜在张载门下求学,大力弘扬张载的“经世致用”“躬行礼教为本”等精神。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钧丁忧返籍, 经与其他兄弟讨论,撰写了《吕氏乡约》。《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为宗旨,重点强调的是个人应加强修身以提升道德,同时坚持读书、治田、营家以改善家庭经济。《吕氏乡约》规定了乡人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内容涵盖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等。《吕氏乡约》还规定,乡人应根据彼此能力患难相恤,需要互相扶助的情形具体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项。
《吕氏乡约》推行后,取得了一定效果。《宋史·吕大钧传》记载:“后乃行于冠昏、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元丰三年(1080年),著名理学家程颐来关中讲学,对于吕大钧推行乡约颇加称赞,评价为“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蓝田吕氏集》记载,吕大钧去世后,乡人感念,“相率迎其丧,远至数十百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南宋时,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了修订,在“德业相劝”一条中加入“畏法令,谨租赋”的内容,使乡约更符合朝廷对乡村治理的需要。由于朱熹的巨大影响力,其修订后的《吕氏乡约》被更多人知晓。
参与治理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将《吕氏乡约》列入《性理大全》颁示天下,令人诵读,使《吕氏乡约》进一步走向全国。嘉靖八年(1529 年),在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建议下,朝廷颁布了关于乡约订立以及对抗拒乡约者如何制裁方面的规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六谕》作为订立乡约的主要参考依据,其内容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等方面,规定举行乡约时要捧读明太祖的《教民榜文》。这些举措表明,朝廷希望乡约在教化百姓的同时,还能承担一部分乡村治理方面的实务。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他一向重视社会教育,到任后颁布了“十家牌法”等一系列文告,改革风俗、增进教化。3年后,受《吕氏乡约》影响,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共16条,规定乡民共同遵守的一系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与《吕氏乡约》的自由参加不同,《南赣乡约》强调对乡村的全覆盖,如规定不参加乡约者将罚银1两。《吕氏乡约》重点突出的是约长的道德感化角色,而《南赣乡约》的治理色彩更加浓厚,设有约长、约副、约正等,分别明确他们的职责,包括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劝导有过错的乡民改过自新、协助官府维护地方治安等。与《吕氏乡约》相比,《南赣乡约》内容更广泛、组织更严密、职责更清晰,表明其已参与到乡村的实际治理中。《南赣乡约》后来被朝廷推广,曾在明朝任知县的叶春及在《惠安政书》中记载:“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
明朝万历年间,吕坤巡抚山西地方,在此期间有感于乡间有重武轻文之风,于是提出将乡约与保甲制度结合来,以加强乡村治理。为此,吕坤撰写了《乡甲约》,将乡约、保甲纳入同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中,规定:“以一里为率,各立约正一人,约副一人,选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统一约之人。约讲一人,约史一人,选善书能劝者充之,以办一约之事。十家内选九家所推者一人为甲长。”在这个体系中,“约”成为一个组织单元,每里设一约,置约正、约副、约讲、约史等,他们都属于义务性质,没有官府配备的办公场所和经费,故尔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多为家境殷实者,或从属于家族、书院。各约之上还设有监督管理机制,官府通过其监管各约。
明朝对乡约十分重视,除《南赣乡约》《乡甲约》和叶春及在任职广东惠安知县期间推行的乡约外,胡直的《求仁乡约》、李春芳的《订乡约事宜》、唐灏儒的《葬亲社约》、黄佐的《泰泉乡礼》等也较为知名。到了清朝,对乡约仍十分重视,如顺治二年(1645 年) 颁布的《逃人法》规定“即将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这里把乡约长与保甲等都作为追查逃匿人员的责任人。康熙年间,规定举行乡约时要将“讲谕”与“读律”结合起来。根据清人陈秉直所著《上谕合律乡约全书》,其程序是:举行乡约时, 在讲解完圣谕“敦孝悌以重人伦”等后,紧接着“读律”,即讲解律法。这样做既能辅助乡约的宣讲效果,也能在乡民中普及朝廷律法。
在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乡约通常都能受到官府与民间的共同认可。大多数情况下,乡约与法律并不矛盾,前者是对后者的有效补充。乡约一方面体现了乡村社会的道德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又统筹整合了乡村的救灾济困、抚恤孤弱、诉讼调解、维护治安等诸多实务,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乡村治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