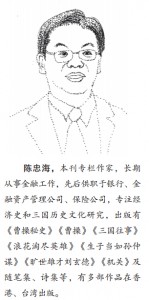作者: 陈忠海
中国的人口总数由商周时期的千万左右发展到清末的4亿,其过程并非等量增长,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和爬升,重要的梯级有1000万、5000万、1亿等。造成人口梯级性增长的原因,除政治、军事甚至气候变化等因素外,经济因素无疑更为重要。
千年徘徊
关于人口增长的规律马尔萨斯有一个著名理论,认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会增加一倍。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即使把西汉时期的公元元年中国人口总数假定为1000万,到公元5世纪初的东晋时总人口就会突破1万亿了,但事实上这两个时期的人口数却没有太大差别。
马尔萨斯认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以几何级速率增加,但生活资料却以算术级速率增加,一个是2、4、6、8……,一个是1、2、3、4……,按照这个速率,只需经过200年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例将会达到256:9,300年是4096:13,生活资料是制约人口自然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先秦时期的人口总数一直处在低位徘徊阶段,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夏代的人口约1300万,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到战国末期仍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秦统一时人口总数估计为2000万左右。2000年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但人口总数却基本保持了稳定,原因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的约束。
这一阶段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出现了粟、黍等被驯化栽培的农作物,青铜农具代替了石质农具,又初步掌握了物候知识和天文历,农业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为养活上千万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还处在粗放和落后阶段,作物品种单一,青铜农具存在很多缺陷,缺乏水利基础设施保障,生活资料的增长受到极大制约,加上战乱、自然灾害等,人口始终维持在同一水平。
农业突破
中国第一次人口梯级出现在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总人口数达到了5900万,西汉末年人口数虽然锐降,但到了东汉初期又快速回升,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人口总数为3400万,章帝章和二年(88年)为4300万,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为5300万,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为5600万。
两汉300多年间人口总数大体在5000万上下波动,较夏商周三代有了质的突破,除了统一王朝带来的社会稳定以及战争的减少外,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是最关键原因。
汉代进入中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期,农业由粗放逐步向精细发展,农具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铁犁壁、二人三牛的耦犁以及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先进生产工具,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耕作的速度和质量都大为提高,农作物品种也更为丰富,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的传递,大量新品种农作物被引进,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也更加重视,出现了更为精确的历法,这些使得徘徊了200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质的飞跃。
夏商时的粮食亩产量缺少文献记载,《管子》说过“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这说是春秋时期的产量,亩产20钟,1钟为10石,即亩产2石。《汉书•食货志》有关于战国时期粮食亩产的记载:“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即亩产1.5石。由于计量单位的变化,这些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考证,到战国后期大豆的亩均产量约61.5公斤,粟的亩均产量约108公斤。
汉代粮食亩产量有了突破性提高,《前汉纪》谈及西汉文帝时的亩产:“今夫农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产3石。《史记•河渠书》讲五千顷耕地“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5000顷合50万亩,即亩产4石。汉末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通称之也。”1斛即1石,这里说亩产10石,不过不是粮食的普遍产量,而是“良田”。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粮食单产较先秦时期有了较大提高,《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估算,汉代粟的亩产量超过了140公斤。
重心南移
汉代人口达到5000万梯级后又出现了新的徘徊,其间发生的战争固然对人口变化有一定影响,但新的峰值出现后便不再进一步突破,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对人口的支撑作用又出现了新的瓶颈。
魏晋以后国家出现分裂,人口一度出现了波谷,据《中国人口史》推测,三国时期人口总数在1400万-1800万之间,西晋的人口总数约2000万,随后人口出现了缓慢回升,南北朝人口最鼎盛时达到了4200万,隋统一时约为4900万。
从汉末到隋初,人口重回5000万梯级用了300多年,与大一统时期的两汉不同,这段时间国家处在更大的分裂与动荡之中,政权分割,战事频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严重制约了人口增长,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人口总数重新回升,得益于经济重心的南移。
晋代之前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广大南方地区虽然早已纳入国家版图,但那里地广人稀,多属未开化之地,一直到汉末,黄河流域都是人口密集区,据《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东汉时的公元140年,今河南省辖区内人口约923万、山东省约863万、河北省约638万,而同期江苏省约222万、浙江省约81万、广东省约86万。
从西晋末年开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气候较热,土地肥沃,更适合耕种,北方地区虽开垦较久,但潜力已经不大,且战乱多发,迫使大量人口南迁。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全国耕地面积在6.9亿亩至8.2亿亩之间,如果考虑到统计的误差,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应当大体保持不变,而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全国耕地面积一下子跃升到19.4亿亩,增加了一倍还不止,多出来的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长期开发江南所增加的。
汉末至隋初数百年的战乱虽然严重削弱了生活资料的供给,但江南的开发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所以人口总数才能重新回到5000万的梯级。
结构矛盾
唐宋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社会相对稳定,而且江南的开发进一步持续,这为生活资料的不断积累创造了条件,在社会总供给量不断增加的推动下,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到宋朝时人口总数跃上了1亿的新梯级。
在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的情况下,养活1亿人并非易事,除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水稻等新品种作物的进一步推广外,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尤其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功不可没。据《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南宋时今江西省辖区内的人口达到了1025万,而同期河北省仅为466万,江南地区后来居上。
1亿的人口梯级一直保持到清初,抛开其间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暂时人口下降外,人口总数基本上又稳定了数百年,人口增长出现新的停顿,意味着生活资料供给又出现了新的瓶颈。
在此之前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并非唯一构成,自然经济条件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所谓“生活资料”,也并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宋、明之间人口出现了新的徘徊,与经济结构矛盾不无关系。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意味着供需矛盾出现了新变化,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消费变化更能说明问题。
明朝中期开始,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一些原本只有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从饮食消费看,一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讲究起来;从服饰消费看,人们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服饰制度,富裕人家竞尚奢华;从住房消费看,不仅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兴起了“园林热”,由士人带动、富商跟进,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除此之外还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这种“消费升级”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不无关联。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工业革命,传统农业已退出经济的主导地位,手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这种现象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
但是,中国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却没能跟上这个潮流,由于经济政策的保守和失误,明朝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总体是失败的,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了国家经济90%以上的份额,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升,整个明朝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3%,不仅经济总供给量不足,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历史有巧合,但更多情况下是必然。政治的好坏、战争的胜负以及关键历史人物的出现固然可以影响王朝更替的频次和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把时间的维度拉长到百年、千年以上,就可看出一些更为宏观的规律来。
从数千年中国人口增长的几次梯级变化可以看出,真正起制约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又不可能永远按照一个速度持续向前,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取得一次突破后又会遇到新的瓶颈,形成新的“供给约束”,这大概才是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
新的“供给约束”既有量的一面,也有质的一面,当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时,影响人口增长的“生活资料”便出现了新的内涵。改善供给既要重量也要重质,这使突破“供给约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每一次梯级性突破都会迎来数百年持续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