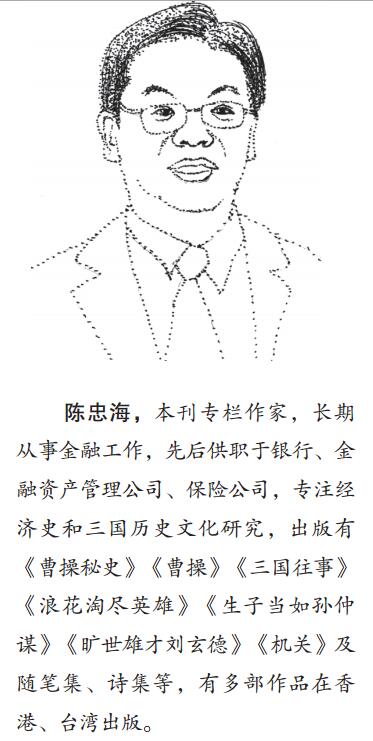陈忠海
鸦片战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大笔军费支出和巨额战争赔款让本已拮据的财政更加不堪重负,恰在此时又爆发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财政体系面临崩溃。仓促之下清政府推出了厘金制度,虽部分缓解了财政困境,却也断送了重新振起的最后希望。
屋漏逢雨
长期以来,清政府的财政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为了支付额外的军费和巨额战争赔款,道光、咸丰两任皇帝都想尽了办法,咸丰皇帝更通过一场“币制改革”搜刮去数千万两社会财富,勉强支撑着危局。
但咸丰朝的“币制改革”因先天不足而失败,未能形成为财政源源输血的长效机制,清政府的财政困境仍未摆脱。为了筹钱,咸丰皇帝想尽了办法,如下令停发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官员的部分俸银,裁撤养廉银,重开捐输,甚至把府库里的三口金钟都拿来铸成了金条,但这些都杯水车薪。
财政问题带来连锁反应:由于财力不足,赋税征收的力度就不断加大,加上清查历年“积欠”,激化了社会矛盾;还是由于财力不足,清政府的基层权力体系被削弱,地方逐步“空心化”,加上社会矛盾尖锐,造成天地会、哥老会等帮会势力的兴起,并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让清政府措手不及,与丢城失地相比,一个更严峻和头痛的问题摆在咸丰皇帝面前:为镇压太平军又要支付巨额军费,从哪里来?咸丰三年(1853)户部奏称:“自广西用兵以来,奏报军晌及各省截流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两,各省地丁、盐课以及关税、捐输,无不日形支绌。”大学士文瑞的奏折更让咸丰皇帝看了触目惊心:“现在户部库存不过支三、四两月,兼之道路梗塞,外解不至,设使一旦空虚,兵饷亦停,人心猝变,其势岌岌不可终日。”
别的钱可以拖,兵饷却不能拖,拖则生变,这个道理咸丰皇帝懂,但是办法在哪里呢?
病急投医
在清政府财政收入里,地丁是大项,其次是盐税、关税,这几样都是着急办不来的,况且太平军攻城掠地后大片地区“沦陷”,税基大减,即使能收上来也较常年大为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开辟新的税种,具体说是一种新的商业税。据《清代钞档》,新税种拟对经商的上等铺户每月征银2钱,中等铺户每月征银1钱,小本下户及工匠等免征,等于是国家对中、上等铺户收取“月租费”,该办法计划先在北京试行,之后推广到各省城,再推广到各州县。
然而试行并不顺利。咸丰三年(1853)2月,新税种还未开征,仅向商户传达了有关律令,京城各家钱铺、粮店等便以闭市作对抗,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当时是非常时期,任何惊扰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期的动荡,清政府赶紧收回成命。
正当咸丰皇帝和大臣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来自江苏前线的一份奏折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这份奏折提出了一个筹钱的好办法。
上奏折的人叫雷以諴,咸丰三年(1853)初,他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会同河道总督杨以增巡视黄河,事毕雷以諴主动上奏“杀贼自效”,得到批准。雷以諴“广延豪俊,捐资募勇,自成一军,扎营扬州东南之万福桥”,此时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建江北大营以对付太平军,雷以諴所部归琦善节制。
按理,雷以諴所部的经费应由琦善解决,但琦善正为自己的军费发愁,哪能顾得上一支杂牌军?雷以諴所部“尤无取资处”,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一个名叫钱江的浙江监生跑来向他献策:“不请饷而抽厘,其事必集。”一语点醒雷以諴,于是想出了收取厘金筹措军费的办法,该办法在扬州仙女庙、邵伯等地试行,效果很好。
所谓厘金,就是向商户和商品征税,最初的想法是“每百分仅捐一分”,一分又是一厘,故称“厘金”。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高兴,立即着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等人“各就江南、江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办事效率一向很低的清政府这次动作却很快,当年11月,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胜保奏请在各省推行厘金制度;咸丰五年(1855)4月,湖南巡抚骆秉章办起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8月,以兵部侍郎身份在江西督办军务的曾国藩也在江西试办厘金;11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湖北试行;12月,四川总督黄宗汉在四川创办厘金。
到咸丰七年(1857),全国各省基本上都开征了厘金。
各行其是
厘金分两种,一种是“坐厘”,类似于商品税和交易税,另一种是“行厘”,类似于通过税。也就是说,无论货物在本地还是异地销售,不仅本地要收钱,而且在贩运途中所经之地也要收钱,而后面这种“通过税”更是厘金的大头。
征收的对象最早是米、盐、布匹等日常所需物品,后来扩展到几乎所有品类,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和土药厘四种,其中“洋药厘”专指进口鸦片厘金。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对江苏、广西、浙江等省的统计,每省收取厘金的商品多达数百至上千项。收取的比率也很快突破了1%的设计,根据商品种类不同,各地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比率,江苏的平均费率为5%,广东为7%,福建高达10%。
一开始,厘金征收多由隶属军需部门的各省粮台、军需局、筹铜局等代理,随着征收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省都设立了厘金局,有的也称厘捐局、捐厘局、税厘局等,省里设总局,府县及口岸分设大大小小的分局、分卡,配巡队、巡船,形成“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的局面。据《清会典事例》,仅湖北一省所设立的厘金局、卡,最多时就达到了480多处。
厘金的征收迅速解决了军费这个燃眉之急,据有关史料统计,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共报销军费2000余万两,其中由厘金支出的就高达1600万两左右。
站在公共财政的立场看,这时候收取的厘金还不能称为“税”,而只能是一种收费。税收是筹集财政收入的形式,而收费是政府有关部门为机构和个人提供特定服务而向直接受益者收取的代价。税收的主体是国家,收费的主体是行政部门;税收具有无偿性,收费则用于成本补偿的需要;税收由国家列入预算统一安排,而收费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
以筹集军饷为初始目的的厘金未能及时纳入政府的预算中,在征收工作中,各地执行办法不一,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各省的总局委员由督抚任命,户部的官员铨选规则在此失效,征收和管理的权力基本上也在地方手中,以至于各地实际征收了多少朝廷也不能真实掌握。从这些情况看,厘金只是一种收费,还是一种“乱收费”——充满着混乱的收费。
得不偿失
厘金制度虽然帮助清政府暂时渡过了财政难关,让其没有立即倒在太平天国的面前,但该制度的推行却从多个方面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经济,让清政府从此再无翻身的可能。
首先,厘金的征收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进行。各地遍设局、卡,过则收费,形成一个个内部的“贸易壁垒”。有人做过统计,要把湖北的砖茶运到内蒙古,一路上须交厘金及正常关税13次,把羊毛从包头运往北京要交17次。从自贡到重庆一路上有局、卡21个,从涪陵到重庆有16个,在苏州的大运河上“几乎每隔10英里就有一个厘卡”。商户还常受到官员刁难,反复翻检货物,耗费大量时间。
其次,厘金的征收抬高了商品和原材料价格。 据1874年10月《申报》的一则报道,苏州和上海短短一点儿距离商贩就要“报捐”3次,交纳的厘金“适当资本的二成或三成不等”,如果运到更远的地方,厘金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可想而知。商品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另一方面提高了原材料价格,损害了本已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再次,厘金的征收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为鼓励对外贸易,一般国家都会实行税收保护主义政策,对本国商品实行税收优惠而对别国商品加重税率,清朝政府则相反,在列强的挟迫下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降低国外产品的关税,并在相关条约中规定洋货“自在某港按例纳税之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也就是洋货免征厘金。本国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都承担着沉重的税费,严重削弱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为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政治上说,厘金制度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开征厘金后,清政府的财权不断下移,以奏销制、协留款制为核心的“收支两条线”制度名存实亡,地方督抚财权扩大,并进一步向人事权延伸,削弱了中央集权,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有实力的地方督抚纷纷崛起,其基础就是从办厘金开始的。
站在清政府的角度,如果应对得当也许是另一种局面。道光、嘉庆时期清朝仍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和排名前列的经济规模,商业、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但朝廷税收体制沿续着千百年来习惯的做法,即以土地税、盐税为主体,商业税微不足道,因此造成了财政的贫乏。根据当时的情况,改革税收体系、增加商业税征收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清政府缺乏这方面的远见和规划,情急之下草草推出的新税又因遭到抵制而不了了之。当初,如果通过科学的规划把厘金变成正常的商业税收,制定全国统一的征收规则,组建统一的征收队伍,把收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统一安排,钱一样收上来了,而情况或许没有这么糟。
一场大规模的“乱收费”虽然部分解决了清政府的财政难题,延续了王朝的寿命,但也制约了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断送了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