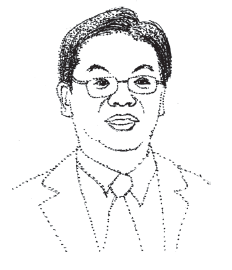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在后人眼中司马光的身上贴有保守主义的标签,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似乎代表了他对改革的全部态度。然而,作为一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朝廷重臣,司马光的思想远非“保守”就能概括的,比如他在财政管理方面的思想就不失丰富和深刻。
以义理财
中国儒家对“义”和“利” 有着全面的认识,孔子的“重义轻利”,孟子的“义利两分”,墨子的“贵义尚利”,都是在不否认“利”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义” 更加重要,这种传统义利观不仅是道德和伦理规范中的重要标尺,也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观。
司马光是儒家传统义利观的继承者,作为朝廷重臣,他的义利观更具务实性,在他所上的《论财利疏》中,对于用何种义利观来指导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进行了论述,一方面指出“求利所以养生”,强调“利”对于百姓和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衣食货赂,生养之具,争怨之府”,甚至“民常以利丧其生”,强调过于重利、唯利是图带来的弊端。司马光认为应通过“义”来约束和规范“利”,将“义”作为追求“利” 的前提和准绳,司马光将上述义利观概括为“利以制事,以义制利”,这种思想与荀子的义利观更为相近,这也是司马光理财思想的集中反映。
当然,“义”不是空洞或虚无的,更不是一句口号,司马光心中的“义”有具体所指,他提出“安民勿扰,使之自富”,他对此解释为: “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 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在传统儒家看来, 重义与民本是一脉相通的,既是道义担当,也有利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正如司马光指出的那样:“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 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
“富民”其实就是司马光心中的“义”,众所周知,王安石在这方面的主张是“富国”,并以此作为变法的根本宗旨,表面看来二者殊途同归,其实有不小的差别, 这两个目标要同时实现,必须寻找到最恰当的平衡点,而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偏激的举措恰恰破坏了平衡。
《论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司马光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财者反此。”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等人属于“不善治财者”,他们的做法是涸泽而渔,是害民、伤民和病民。
其实,王安石并非不想“富民”,许多变法措施其实也兼具了“富民”的目标,但由于宋初以来就存在的“三冗两积”问题已十分严重,迫切需要一剂“猛药”来医治沉疴,而传统方法难以尽快见效,所以一些做法就不得不激进了,但如此以来也会带来社会承受能力的巨大风险,这是司马光最为担心的。
养本取财
理财的前提是生财,都说“生财有道”,但对于何为“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分歧更大的地方。
王安石强调“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个目标当然具有极大的诱惑性,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正是宋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但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国用”和“民不加赋”其实是矛盾的,二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王安石在变法中更多地是运用技术性手段使财富重新分配,以实现“国用”迅速增加的目标,比如均输法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生产、流通方面的控制以直接增加朝廷收入,募役法是通过改革赋役制度来增加收入,青苗法则因执行中的走样最终蜕变为国家以高利贷牟利的工具,惠民、利民的色彩慢慢消退。
司马光的理财主张不同,他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他批评王安石等人的做法是“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司马光主张保养财源,提出“养其本源而徐取之”,也就是先发展生产再增加税收。在发展经济方面,司马光认为各行各业都很重要,他提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司马光认为各行业如果都能得到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到那时“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在“富民”的同时也实现了“富国”目标。
百业之中,司马光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不仅从经济的视角看待这件事,还强调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兴亡,司马光除在一些奏疏中多次提到相关观点,还利用编纂《资治通鉴》的特殊机会以史为鉴,强调失去民心的危险性,《资治通鉴》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各朝代百姓反抗过重剥削而发生起义的史实, 得出“民者,国之堂基也”的结论。在治国实践中,司马光主张宽恤百姓,提出“凡农民租税之外, 宜无有所预”的建议。
简单来说,司马光的生财之道是“向生产要效益”,而王安石的生财之道是“向管理要效益”, 一个强调的是增量,一个强调的是存量,这决定了二人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他主张的改革是有限度的,比如他并不反对方田均税法里的一些内容,主张“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也就是根据资产状况适当调节不同阶层的财政负担比重,使财政负担落在真正有财力的人身上。然而,司马光的渐进式改革无法满足宋神宗急于清除积弊的需要,在宋神宗看来,还是王安石的改革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用财有节
管理国家财政与百姓理财在基本道理上是相通的,无外乎开源和节流两种途径,在一般人看来,主张开源是积极进取的行为,主张节流则偏于保守。
与主张开源的王安石不同, 司马光更主张节流。司马光多次指出,财政支出过大既是“三冗两积”问题造成的结果,也是其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当时财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有5个,即“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多求不如省费”,也就是“减损浮冗而省用之”。
王安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承认财政困难的现状,但认为其原因在于“理财未得其道”,他的解决办法是“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熙宁元年(1608),司马光提出在财政状况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应取消皇帝郊祀时赏赐大臣金帛的惯例,认为“方今国用不足, 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但王安石反对这个做法,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损朝廷的形象。
在财政支出方面,司马光遵循传统量入为出的思想,强调“损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闻古之圣王,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他认为“减节用度,则租税自轻,徭役自少,逋负自宽,科率自止”。作为朝廷重臣, 司马光还从自身做起,注意廉洁节俭,平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他教导儿子说生活中只要“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就行了,司马光死后家无余财,“床箦萧然,惟枕间有《役书》一卷”。
减省支出必然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不减少支出的情况下又能解决财政问题岂不更好?然而,事实证明后者只是一种空想,经过一场变法,宋朝的财政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北宋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返回头看, 司马光关于财政支出的主张虽然谈不上有多少新意,但在宋初以来财政包袱越背越重的情况下,这些主张其实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财有专主
北宋开国以来,朝廷机构设置呈现混乱、庞杂的态势,出于权力制衡考虑,许多机构出现了层叠,有些需要统一管理的职能也处在分权、分制状态,财政管理也是如此。
按当时的体制,财政主要由“三司使”负责,但是该机构不负责管理宫廷支出,太府寺主管的内藏库、奉哀库也行使了很大的财政权力,而一些职能部门,如兵部、礼部、工部等也都有权任意支出, 形成了“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的奇怪局面。
有权力又不用负总责,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就会提出一些看似合理又缺乏全局观念的计划,这也是宋初以来财政失控的一个原因。针对这种弊端,司马光提出“财有专主”的观点,也就是对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就是设置“总计使”,该职务超越各部,“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者皆统之”,使财政管理由分权向集权改进。
财政管理成效的好坏,还与负责此项工作官员的素质、工作态度有很大关系,财政管理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建立一支有经验、有责任心又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宋朝为防范官员久居一地或久任一职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弊端,官员经常频繁调任,不到几年时间就会“上自三司使,下至检法官,改易皆遍”,司马光认为这也是一项弊端,不符合“财有专主”的原则,他建议把“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列为科举取士的科目之一,扩大财政专门人才的选拔范围,同时强调“久任”,认为“官久于其业而后明, 功久于其事而后成”,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财政官员考核升迁办法。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论争中确实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那是有具体所指的,强调的是某些“祖宗之法”,有人将这句话抽出来使之脱离具体语境,用以概括司马光对改革的全部态度,显然有失偏颇。从对司马光财政管理思想的分析看,他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在为什么而改、怎样去改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这些观点,从现在来看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还真应该来听听他所上的这一课。